2024-1-18 00:56 /
忙里偷闲撰写这篇文章,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去查找相关资料,写作有些仓促,多有疏漏,欢迎指出。改日可能会做格式上和一些细节上的改动。
当佐上睦实目送着女孩乘上列车穿过黝黑的隧道去往现实世界时,她说“好像听到新生儿的声音。”这时,佐上睦实才真正完成了一次分娩。

不通过性行为,更没有在客观层面怀孕,就好比“无性繁殖”,佐上睦实成为了圣母玛利亚一般的“处女母亲”。她成为母亲是在故事伊始——照顾因神秘力量来到这个虚幻世界的,自己未来的女儿。于是这个看似静止的箱庭世界就像是变成了佐上睦实的子宫,而伴随着胎儿(五实)的成长,一场缓缓孕育的胎动发生了。故事的结局是显而易见的:经历漫长的等待和胎动,分娩的时刻最终到来,新生儿注将离开子宫去往现实世界。
从这个角度去回看整部影片,许多问题都迸发出一种充满生命力的解释。
比如为何睦实对待五实的态度会经历一些转变,从一种面对新事物的兴奋、紧张,到些许彷徨甚至做出挣扎的行为,再到真正接纳五实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宛如一个突然要成为母亲的孕妇孕育生命的心路历程——尤其是对于一名14岁未经人事的少女来说,突然,甚至是被迫成为“母亲”是一件极富冲击力的事情。

胎动的过程不仅反映在五实的长大,也反映在睦实子宫所外化形成的世界里,同样也反映在这个世界里的其他个体上:影片进展到后半段,冲突、危机与改变骤起,这种“冲动”与影片前半段的“冷静”是反差巨大的,(事实上影片并没有完整展现那段最开始的压抑的世界)正是因为“胎动”正逐渐变强烈,人们的内心与行动都开始躁动起来,他们都是佐上睦实腹中的“胎儿”。
而如果只是将全部故事当作睦实孕育生命的过程,未免太过狭隘。佐上睦实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接纳自己作为母亲的身份并希望成为一名好的母亲,才是更富有女性力量的表达。
睦实成为母亲需要通过两个相伴的过程,一是通过走向自己母亲的反面,二是通过寻找自己孩子的父亲。
佐上睦实的母亲因为现实原因将她送到佐上家当继女,睦实的母亲是不爱她的孩子的。这些所谓的现实原因不是影片讨论的重点,但是从一开始,睦实迎来孩子的方式就走向她母亲的反面——无性繁殖和有性繁殖,不通过疼痛的分娩,与之相伴的一切物质性困境似乎都被排除——睦实要去爱她的孩子,去做一个好母亲。(尽管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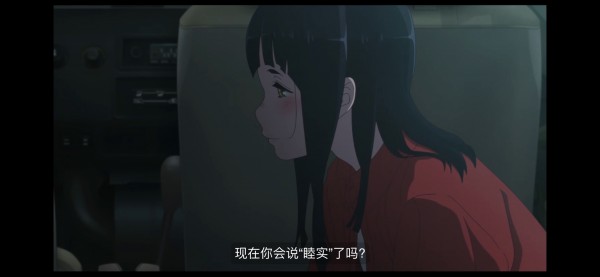
反抗家庭内部的女性地位代际沿袭是反抗父权的传统表达。但在影片中,睦实在走向母亲反面的同时就站到了“父亲”的反面,尽管我们依然能看到佐上对睦实抱有一种大家长式的态度,但睦实却从不把他当一回事。佐上所追求也并不是父性权力的强大,而更多是社会权力的膨胀。这种权力在佐上看来是上天自然给予的,但实则是由五实的力量所带来的。作为其母亲的佐上睦实似乎早就发觉世界的秘密:她的子宫与她的胎儿。睦实作为权力的发送者,在面对权力的接收者时,自然带有一种“胜者”的余裕。
寻找孩子的父亲也并不是找到即可。为了吸引菊入正宗,佐上睦实在天台上掀起自己飘动的裙摆,这个镜头再次揭示了她的余裕与控制力,女性的身体和性征成为可供管理和利用的武器。

这个动作是如此触及正宗那被阉割的男性气质,正宗被吸引是注定的。佐上睦实在有意无意间展现出她少女身躯里承载着的女性力量,而这般力量又被投射到外部的世界中。在他们的同学笹仓(小胖子)口中我们再次发现这个世界里的佐上睦实是如此富有性吸引力。

在寻找孩子父亲的过程中,或者说在形式上“构建家庭”的过程中,二人在感情中的地位由女性主导转向影片结尾的平衡,诚然菊入正宗自身男性性的回归以及他作为父亲的力量的加强也是重要推动因素。但是真正送五实到最后时刻,亲口与五实告别的依然是作为母亲的睦实,不像作为父亲的菊入正宗只能借由沉默的心声传达话语。也依然是因为睦实做出了成为真正母亲的选择:爱自己的孩子也爱自己的丈夫。我们才能看到影片最后睦实压倒正宗撒娇的那一幕。

回到本文最开始对佐上睦实“无性繁殖”的讨论,我们要注意到影片中男性性的剥离与回归。
从笹仓(小胖子)恋物癖的视线中可以看出一种性的本能的变形,正宗在影片前半段各种女体化的展示也是直接对他男性气质进行阉割。到了影片的后半段,男性性似乎开始回归,菊入时宗的告白、孩子间的恋爱、正宗与睦实在雪地上的深吻……然而这依然是受女性左右的,正宗妈妈的拒绝、原的主动告白、以及睦实的默许……我们所看到的男性性依然是被包装着的。

劳动的差异是能很好区分男女力量的方式。影片中女性唯一被强调的劳动是睦实照顾五实的照料性劳动,而男性的劳动则被剥夺得更彻底——哪怕是一张工厂中充满男人的画面,我们依旧无法从破败的工厂中感受到男人真正的劳动,就连开车这样与机械装置连结紧密的活动,在影片中也似乎是每个孩子都会的技能。


工厂的爆炸早就指向工业时代的结束,一种后未来的时代来临了,消耗体力的劳动消失,男性性随之弱化,劳动本身也开始转移和改变。
体力劳动被照料劳动取代,男性被弱化,女性被加强,技术的力量被弱化,自然的力量被加强,一个“母性的乌托邦”被建构起来。(和宇野常宽的“母性敌托邦”有些相似但也有不同之处)
我们在佐上睦实这么一个14岁的“处女母亲”身上看到了母性与少女性的对立统一,最终母性的部分压倒少女性的部分。而佐上睦实身上的对立统一同样也代表这个“子宫”世界里技术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但出人意料的是,影片的结尾展示了一个技术压倒自然的结局,母性的诞生,技术的回归,为何会这样?

很明显,在胎儿离开子宫之前,五实象征着工厂爆炸后,即技术被破坏后展露的自然的力量。五实的心情很大程度左右世界的面貌,她是不断发育的胎儿,其力量既来自于她自身也来自于作为其母亲的睦实。在这种和超自然力量的关系里,五实既是主动的一方也是被动的一方,她既能影响世界同时也受世界威胁——正如“胎动”的过程总是双向的。

这样来看影片的结局便有了一种新的意味:作为胎儿的五实,选择离开子宫,这对于她来说毫无疑问需要一种自我牺牲式的决绝。(同样是痛苦的)

而作为母亲的睦实,从允许正宗将五实带出工厂,再到主动送别五实去往现实世界,这意味着一种接纳和放手。至此,佐上睦实才真正彻底走向其母亲的反面,她让她的孩子摆脱了“罪”的代际传承。(毕竟睦实也曾想将五实一直待在工厂)佐上睦实在真正分娩的同时也引来了自己的新生。
睦实也知道,送走五实代表着这个虚幻的世界终将迎来终结,于是她感恩疼痛,感恩活着是多么美好。这时,真正的自然的生机才重回这个世界。

当我们看到工厂近乎同时的“复工”才发现,由技术维持的生命也属于自然的范畴,技术与自然的对立就此解构,男性与女性的力量也就此平衡。
观影到最后,我想起《风之谷》中的娜乌西卡,她也是一位少女,也是一位“处女母亲”,她的孩子是人造的“巨神兵”。在漫画的最后,她决意带领巨神兵破坏墓所,把世界的终极秘密隐藏于心,与人们(同为人造人们)一起活下去。和这部影片一样,两位母亲的决定都注定带来世界的灭亡。而娜乌西卡做出这个决定的根据就在于“人造人也是生命”。这里就引用一段娜乌西卡的动人台词作结。
“虽然我们的身体是人工制造加工的,但我们的生命是我们自己的生命。生命,用生命的力量活着。如果那个清晨(世界净化日)终将到来,那么我们就迎着它活下去吧。我们是一边口吐鲜血一边反复跨越那个清晨、展翅飞翔的鸟儿!让我们出发吧,无论多苦,必须活着……”



参考文献
《战斗公主 劳动少女》 河野真太郎(日) 赫杨译
没想到24年第一篇日志竟然写冈妈的新片,明明这部动画后一个小时的观影让我受尽折磨……
这部电影在其他方面的探索都不算有新意,后灾难的语境更是只停留在地域表面;要说技术和自然的关系,也只是被男女关系偷换了概念而已。冈妈的作者性仿佛早已胎死腹中。
当佐上睦实目送着女孩乘上列车穿过黝黑的隧道去往现实世界时,她说“好像听到新生儿的声音。”这时,佐上睦实才真正完成了一次分娩。

不通过性行为,更没有在客观层面怀孕,就好比“无性繁殖”,佐上睦实成为了圣母玛利亚一般的“处女母亲”。她成为母亲是在故事伊始——照顾因神秘力量来到这个虚幻世界的,自己未来的女儿。于是这个看似静止的箱庭世界就像是变成了佐上睦实的子宫,而伴随着胎儿(五实)的成长,一场缓缓孕育的胎动发生了。故事的结局是显而易见的:经历漫长的等待和胎动,分娩的时刻最终到来,新生儿注将离开子宫去往现实世界。
从这个角度去回看整部影片,许多问题都迸发出一种充满生命力的解释。
比如为何睦实对待五实的态度会经历一些转变,从一种面对新事物的兴奋、紧张,到些许彷徨甚至做出挣扎的行为,再到真正接纳五实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宛如一个突然要成为母亲的孕妇孕育生命的心路历程——尤其是对于一名14岁未经人事的少女来说,突然,甚至是被迫成为“母亲”是一件极富冲击力的事情。

胎动的过程不仅反映在五实的长大,也反映在睦实子宫所外化形成的世界里,同样也反映在这个世界里的其他个体上:影片进展到后半段,冲突、危机与改变骤起,这种“冲动”与影片前半段的“冷静”是反差巨大的,(事实上影片并没有完整展现那段最开始的压抑的世界)正是因为“胎动”正逐渐变强烈,人们的内心与行动都开始躁动起来,他们都是佐上睦实腹中的“胎儿”。
而如果只是将全部故事当作睦实孕育生命的过程,未免太过狭隘。佐上睦实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接纳自己作为母亲的身份并希望成为一名好的母亲,才是更富有女性力量的表达。
睦实成为母亲需要通过两个相伴的过程,一是通过走向自己母亲的反面,二是通过寻找自己孩子的父亲。
佐上睦实的母亲因为现实原因将她送到佐上家当继女,睦实的母亲是不爱她的孩子的。这些所谓的现实原因不是影片讨论的重点,但是从一开始,睦实迎来孩子的方式就走向她母亲的反面——无性繁殖和有性繁殖,不通过疼痛的分娩,与之相伴的一切物质性困境似乎都被排除——睦实要去爱她的孩子,去做一个好母亲。(尽管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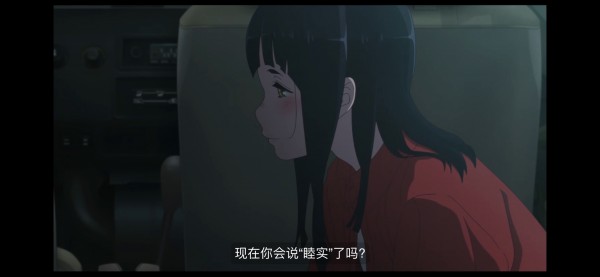
反抗家庭内部的女性地位代际沿袭是反抗父权的传统表达。但在影片中,睦实在走向母亲反面的同时就站到了“父亲”的反面,尽管我们依然能看到佐上对睦实抱有一种大家长式的态度,但睦实却从不把他当一回事。佐上所追求也并不是父性权力的强大,而更多是社会权力的膨胀。这种权力在佐上看来是上天自然给予的,但实则是由五实的力量所带来的。作为其母亲的佐上睦实似乎早就发觉世界的秘密:她的子宫与她的胎儿。睦实作为权力的发送者,在面对权力的接收者时,自然带有一种“胜者”的余裕。
寻找孩子的父亲也并不是找到即可。为了吸引菊入正宗,佐上睦实在天台上掀起自己飘动的裙摆,这个镜头再次揭示了她的余裕与控制力,女性的身体和性征成为可供管理和利用的武器。

这个动作是如此触及正宗那被阉割的男性气质,正宗被吸引是注定的。佐上睦实在有意无意间展现出她少女身躯里承载着的女性力量,而这般力量又被投射到外部的世界中。在他们的同学笹仓(小胖子)口中我们再次发现这个世界里的佐上睦实是如此富有性吸引力。

在寻找孩子父亲的过程中,或者说在形式上“构建家庭”的过程中,二人在感情中的地位由女性主导转向影片结尾的平衡,诚然菊入正宗自身男性性的回归以及他作为父亲的力量的加强也是重要推动因素。但是真正送五实到最后时刻,亲口与五实告别的依然是作为母亲的睦实,不像作为父亲的菊入正宗只能借由沉默的心声传达话语。也依然是因为睦实做出了成为真正母亲的选择:爱自己的孩子也爱自己的丈夫。我们才能看到影片最后睦实压倒正宗撒娇的那一幕。

回到本文最开始对佐上睦实“无性繁殖”的讨论,我们要注意到影片中男性性的剥离与回归。
从笹仓(小胖子)恋物癖的视线中可以看出一种性的本能的变形,正宗在影片前半段各种女体化的展示也是直接对他男性气质进行阉割。到了影片的后半段,男性性似乎开始回归,菊入时宗的告白、孩子间的恋爱、正宗与睦实在雪地上的深吻……然而这依然是受女性左右的,正宗妈妈的拒绝、原的主动告白、以及睦实的默许……我们所看到的男性性依然是被包装着的。

劳动的差异是能很好区分男女力量的方式。影片中女性唯一被强调的劳动是睦实照顾五实的照料性劳动,而男性的劳动则被剥夺得更彻底——哪怕是一张工厂中充满男人的画面,我们依旧无法从破败的工厂中感受到男人真正的劳动,就连开车这样与机械装置连结紧密的活动,在影片中也似乎是每个孩子都会的技能。


工厂的爆炸早就指向工业时代的结束,一种后未来的时代来临了,消耗体力的劳动消失,男性性随之弱化,劳动本身也开始转移和改变。
体力劳动被照料劳动取代,男性被弱化,女性被加强,技术的力量被弱化,自然的力量被加强,一个“母性的乌托邦”被建构起来。(和宇野常宽的“母性敌托邦”有些相似但也有不同之处)
我们在佐上睦实这么一个14岁的“处女母亲”身上看到了母性与少女性的对立统一,最终母性的部分压倒少女性的部分。而佐上睦实身上的对立统一同样也代表这个“子宫”世界里技术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但出人意料的是,影片的结尾展示了一个技术压倒自然的结局,母性的诞生,技术的回归,为何会这样?

很明显,在胎儿离开子宫之前,五实象征着工厂爆炸后,即技术被破坏后展露的自然的力量。五实的心情很大程度左右世界的面貌,她是不断发育的胎儿,其力量既来自于她自身也来自于作为其母亲的睦实。在这种和超自然力量的关系里,五实既是主动的一方也是被动的一方,她既能影响世界同时也受世界威胁——正如“胎动”的过程总是双向的。

这样来看影片的结局便有了一种新的意味:作为胎儿的五实,选择离开子宫,这对于她来说毫无疑问需要一种自我牺牲式的决绝。(同样是痛苦的)

而作为母亲的睦实,从允许正宗将五实带出工厂,再到主动送别五实去往现实世界,这意味着一种接纳和放手。至此,佐上睦实才真正彻底走向其母亲的反面,她让她的孩子摆脱了“罪”的代际传承。(毕竟睦实也曾想将五实一直待在工厂)佐上睦实在真正分娩的同时也引来了自己的新生。
睦实也知道,送走五实代表着这个虚幻的世界终将迎来终结,于是她感恩疼痛,感恩活着是多么美好。这时,真正的自然的生机才重回这个世界。

当我们看到工厂近乎同时的“复工”才发现,由技术维持的生命也属于自然的范畴,技术与自然的对立就此解构,男性与女性的力量也就此平衡。
观影到最后,我想起《风之谷》中的娜乌西卡,她也是一位少女,也是一位“处女母亲”,她的孩子是人造的“巨神兵”。在漫画的最后,她决意带领巨神兵破坏墓所,把世界的终极秘密隐藏于心,与人们(同为人造人们)一起活下去。和这部影片一样,两位母亲的决定都注定带来世界的灭亡。而娜乌西卡做出这个决定的根据就在于“人造人也是生命”。这里就引用一段娜乌西卡的动人台词作结。
“虽然我们的身体是人工制造加工的,但我们的生命是我们自己的生命。生命,用生命的力量活着。如果那个清晨(世界净化日)终将到来,那么我们就迎着它活下去吧。我们是一边口吐鲜血一边反复跨越那个清晨、展翅飞翔的鸟儿!让我们出发吧,无论多苦,必须活着……”



参考文献
《战斗公主 劳动少女》 河野真太郎(日) 赫杨译
没想到24年第一篇日志竟然写冈妈的新片,明明这部动画后一个小时的观影让我受尽折磨……
这部电影在其他方面的探索都不算有新意,后灾难的语境更是只停留在地域表面;要说技术和自然的关系,也只是被男女关系偷换了概念而已。冈妈的作者性仿佛早已胎死腹中。
#1 - 2024-1-20 17:40
坂本喜八君 (生存模式中。)
#1-1 - 2024-1-20 17:56
Somnus、R
感谢回复,最近会去读读这篇,有感想的话会再回复
